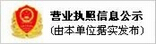克勞塞維茨在《戰(zhàn)爭論》中說:“軍事權(quán)力必須予以毀滅,那也就是要把它減弱到一種不能再作戰(zhàn)的狀況;國家必須加以征服,因?yàn)閲抑畠?nèi)又可能再組成一支新的軍事力量。但即便上述二者均已做到,只是敵人的意志尚未征服,戰(zhàn)爭還不能算是已經(jīng)結(jié)束;那也就是說,敵國政府及其同盟國應(yīng)該被迫簽訂和約,又或其人民都以投降;否則即便我們已經(jīng)占領(lǐng)其國家,在其內(nèi)部或由于其同盟國的援助,戰(zhàn)爭仍有再起之可能。而且毫無疑問,在簽訂和約之后也還是可能如此,總之,任何戰(zhàn)爭的本身并不包含一種完全決定和***解決的因素在內(nèi)。”
廣告目標(biāo)同樣包括三個方面,其一,必須盡量消除受眾對廣告的抗拒心理;因?yàn)椴幌@種抗拒心理,廣告說什么都是徒勞,就算是完全免費(fèi)的產(chǎn)品他也未必會相信。反之,那些因?yàn)閯?chuàng)意太出色而將產(chǎn)品淹沒的事件也是歷歷在目。其二,必須使消費(fèi)者覺得除了廣告產(chǎn)品,沒有其它更好的選擇;讓消費(fèi)者充分認(rèn)識產(chǎn)品的優(yōu)勢。其三,不斷施與友好的情感和刺激,以形成默認(rèn)和忠誠的態(tài)度,只是切記沒有永遠(yuǎn)的忠誠,你應(yīng)該持續(xù)努力。單獨(dú)看這三個方面其中之一,似乎并不困難也不令人感到新鮮,綜合起來考慮則沒那么容易做到,精神世界和情感反應(yīng)并不是那么顯而易見和確實(shí)掌握。
事實(shí)上,在廣告運(yùn)動中的消費(fèi)者一點(diǎn)也不亞于一個裝備精良的交戰(zhàn)國,消費(fèi)者每天都要經(jīng)歷上千次的廣告“轟炸”,他們擁有***精巧和本能性的“防御體系”,或許還有意志相投的強(qiáng)大的戰(zhàn)略盟友,他們所筑起的心理防線固若金湯。這一點(diǎn)非常重要,我們要“解除對手的武裝”并不是要他們“繳械”——掏出緊揣著的鈔票,而是突破消費(fèi)者的心理防線,解除精神的武裝。另外,任何一場戰(zhàn)爭或精神意志的較量都不是由單方面所構(gòu)成的,而是兩股力量的相互作用,所以廣告運(yùn)動的目的(解除對手武裝)對于雙方都同樣適用,而勝利的天平總是在消費(fèi)者那一邊,只要我們發(fā)起的廣告運(yùn)動未能“擊敗”消費(fèi)者,消費(fèi)者就會不費(fèi)吹灰之力地完全將我們擊潰。廣告***沒有“和平”可言!再者,一個促銷意圖對于不同的人可能產(chǎn)生完全不同的效果,甚至在不同的時(shí)間對于同一個人也可能產(chǎn)生完全不同的效果;所以,消費(fèi)者本身的性質(zhì)應(yīng)該被列為***重要的考慮因素。
五、廣告目的對手段的影響
很顯然,如果消費(fèi)者受到某種精神的鼓動,則廣告的效果會大不相同。常有這種可能,當(dāng)廣告信息和消費(fèi)者之間存在著某種情感聯(lián)系時(shí),即便廣告中只有非常微弱的銷售動機(jī),其所產(chǎn)生效果會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好——事實(shí)上,“是一種完全的爆炸”(這種現(xiàn)象仍需要合理的解釋,我們會在后面詳細(xì)論述)相反的,廣告中明顯和強(qiáng)硬的銷售目的就象戰(zhàn)爭中的極端暴力一樣,我們所施加的“暴力”有多大,所引起的反抗就有多大——“我們向?qū)Ψ剿蟮臓奚。瑢Ψ剿鶎⑹褂玫牡挚故侄我矔 ?rdquo;我們在這里不斷強(qiáng)調(diào)精神的力量,并不是單指某種附加于產(chǎn)品身上的情感性利益,而無視產(chǎn)品本身的功能性特征。產(chǎn)品的物質(zhì)和精神、形象經(jīng)常成為廣告運(yùn)動的兩個極端,無論二者的比例和趨向如何,***重要的是必須明白——“物質(zhì)幾乎不過是一個木柄,而精神才是利刃”。
廣告與受眾之間的溝通,說到底還是依循著心理學(xué)的“法則”。不過這里并不討論廣告心理學(xué)那些抽象的概念和表格、以及所謂的科學(xué)數(shù)據(jù),只需要對一些我們時(shí)常接觸和使用的定義做簡單的比較分析。畢竟,廣告既不是什么藝術(shù),也算不上科學(xué)。
六、廣告的溝通手段
1、廣告不是說服、不是打動
無論是廣告人或廣告主,都一心想著通過對消費(fèi)者的說服將產(chǎn)品推銷出去,然而,卻是這些意欲強(qiáng)加給消費(fèi)者的觀念和做法,加上廣告無休止的重復(fù),引發(fā)了人們普遍的反感。廣告在沒有開始說服之前,就把消費(fèi)者看成了被說服的對象,在這種對立的狀態(tài)下,你愈是強(qiáng)硬推銷,愈是適得其反。這樣的廣告無論你說什么都象在告訴消費(fèi)說,你好好坐在那里一分鐘,看我怎么說服你來買這個產(chǎn)品,其效果可想而知。為此,黃文博先生說:“當(dāng)一位高明的傳教士向群眾布道時(shí),他不會試圖說服大家對神產(chǎn)生信仰,那將使他與聽眾處于一種對立狀態(tài),愈強(qiáng)勢的說服,回激起愈強(qiáng)力的抗拒。即陷入單向傳播的死胡同。”
黃先生認(rèn)為關(guān)鍵在于打動,而非說服。其實(shí),打動和說服并沒有本質(zhì)上的區(qū)別,“說服”采取的是由上而下的高壓姿態(tài);“打動”則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勸服。這兩種極端的態(tài)度,都不約而同地站在消費(fèi)者的對立面,把消費(fèi)者視為停止不變的固執(zhí)的個體。同樣容易陷入“單向傳播的死胡同”。
一般情況下,我們對一個廣告進(jìn)行分析時(shí),都會不自覺地從廣告或廣告人的角度作判斷,能看到的、或希望看到的大都是廣告內(nèi)含的高明的說服或打動技巧。而往往容易忽視被“說服”和“打動”的一方——受眾。消費(fèi)者真的被說服或打動了嗎?其實(shí)未必。一件事物,比如面對一棟樓房,假如你只是站在樓的一面進(jìn)行觀察,就只能通過經(jīng)驗(yàn)和推理判斷說這是一棟樓房,盡管映入你眼簾的只是一堵平面的墻。但如果你到樓房的四周看看,從不同的角度加以觀察。情況就不同了,你將會看到一棟立體的、真實(shí)的樓房。也或許會發(fā)現(xiàn)這其實(shí)只是一堵用來拍戲用的平面的樓房布景。我們不得不這么做,因?yàn)槭鼙娬跇欠康牧硪贿吥亍?br />